□ 武志元
公元1912年2月12日,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,北京城里,寒风凛冽。百姓们忙着置办年货,朝堂上却是忧心忡忡。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,在养心殿里举行。当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宣读完退位诏书后,声泪俱下,撕心裂肺地哭诉着:无颜见列祖列宗。是啊,从顺、康、雍、乾、嘉,到道、咸、同、光、宣十帝,共276年的国祚,就在他们孤儿寡母的手中圈上了句号,能不伤心落泪吗?这里,我所关心的是身为二品大员的会宁进士刘庆笃,当时究竟在不在朝?见证那一幕了没有?
当我阅完周大勇编写的《会宁进士刘庆笃》时,虽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,譬如杂记、追忆之类,但也生发了不少随想与叩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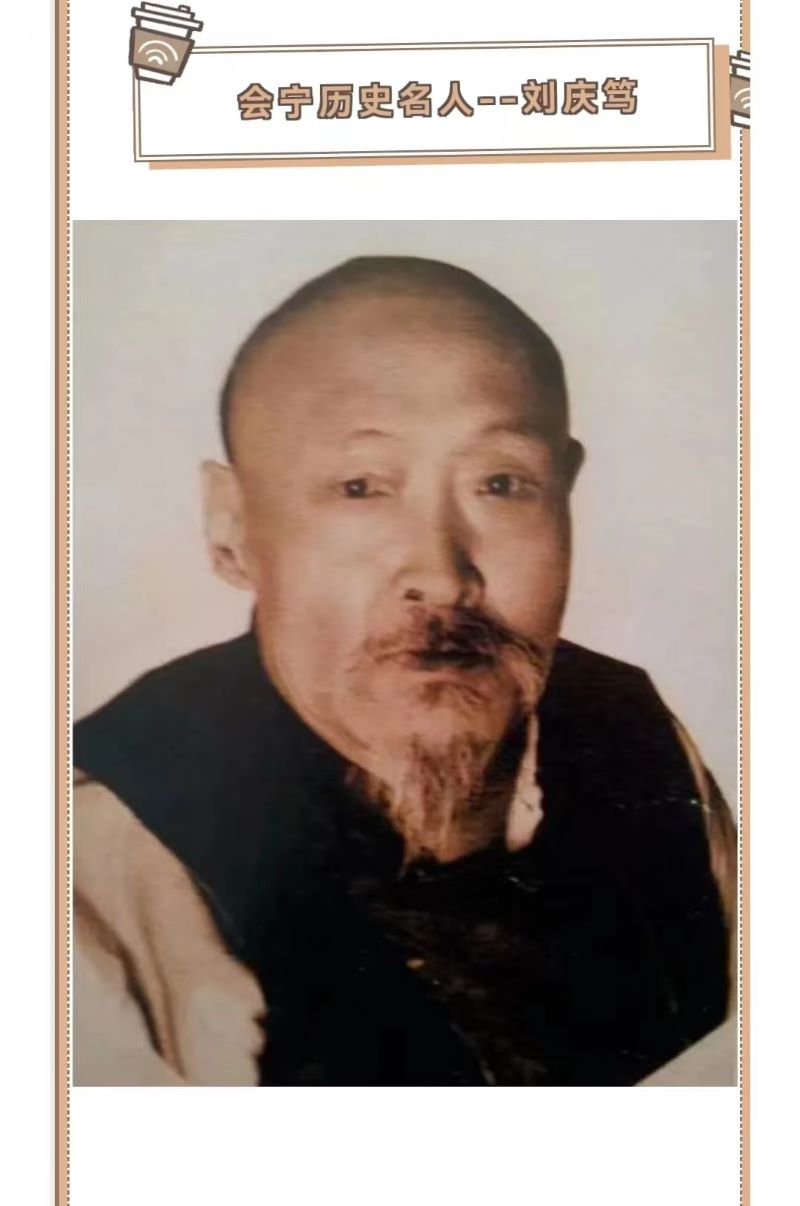
刘庆笃
一、“插天”的文笔
刘庆笃1870年出生在会宁县城东关,父亲为“清吏员”,他自幼聪慧,过目成诵,13岁中秀才,19岁中举人,25岁中进士。陇上名人范振绪称其为“藜阁名家,枝阳世族。初登桂籍,旋讲柳湖,待报捷南宫,遂票签于内阁,是大手笔,入小军机”。奇的是刘庆笃在中举之后的鹿鸣宴上,吟咏的“文笔插天云作篆,词澜浴日艺成龙”的联句,几乎是对自己鸿鹄之志的精准预言。这时的他,踌躇满志,豪气冲天。他成了皇帝身边的“小秘书”,整日里起草谕旨,出纳王命,不是在“文山”中,就是在“会海”里,践行着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的士人信条。
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,刘庆笃学业好、“就业”好,是典型的学霸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,无疑是正确的“废话”。这里我引用一组数据,据科举制度研究者统计,我国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,至少考中进士98749人,其中清代26848人。清代共开考112次(三年一次),平均每次录取进士300余人,也就是每年100人左右。甘肃在清代共中进士343人、会宁20人。掂量这些数字,就可以看出进士的“含金量”,恐怕要远胜当今的“双一流”。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高级精英人才,历史上许多文学家、政治家、大学者,大多是进士出身。
从平均每年100人的录取率,可以想象“文笔插天”,何其难也。姑且不说刘庆笃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的“备考”,也无从查证他究竟有无“头悬梁,锥刺骨”的“寒窗”之苦,单就那时候赴京赶考的旅途颠沛与盘费之大,也非常人所能承受。我们从左宗棠在1873年给朝廷关于陕甘分闱的奏折中看到,甘肃府距西安“近者数百里,远者兰州以西,则三千里或四千里”“边塞路程悠远,又兼惊沙乱石,足碍驰驱,较中原行路之难,奚啻倍蓰!士人赴陕应试,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。所需车驮雇价,饮食刍秣诸费、旅费、卷费,少者数十金,多者百数十金……竟有考生不能赴乡试者,皓首穷经,一试无缘”。
回过头来,我们看今天的高考,考场都设在本县域之内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,今非昔比,让我们感慨良多。
二、历史的悲悯
刘庆笃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,可谓是春风得意,高歌猛进,主要取决于他的“个人奋斗”。但步入社会,许多事就由不得他了。丁忧守制之后,他重返京师,正是三十而立,宏图大展时,怎奈庚子国破,八国联军进北京,慈禧、光绪一干儿人马跑到西边“打猎”去了,他也随扈而行,不离不弃。此时的种种迹象表明,大清已是风雨飘摇,而新桃换旧符,已趋定势。凭他一己之力,难挽狂澜之既倒。掌管晚清权柄47年之久的慈禧已是心殚力竭,骂名滔天。光绪的百日维新,以六君子上断头台而告终。清廷已朽,苟延残喘,四周已布满干柴,正巧遇上了武昌城里那一支枪的意外走火。终于风助火力,挽歌响起,曲终人散。
我们想知道的是,处在风狂雨骤的政治中枢,刘庆笃是帝党呢,还是后党?他是侍奉那个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的皇上呢?还是效忠于那个可恨又可怜的老女人呢?
言说刘庆笃,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慈禧青年丧夫、中年丧子,晚年丧国,是大清的掘墓人,可怜又可恨。当时的外交家郭嵩焘曾用“一味蠢,一味蛮,一味诈,一味怕”的12个字,归纳了晚清外交。洋人的坚船利炮,摧枯拉朽般地击碎了“天朝上国”的梦。慈禧的宿命,应了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写的:“灭六国者,六国也,非秦也。族秦者,秦也,非天下也。”“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慈禧的乾纲独断,导致了清廷的覆亡,也给刘庆笃的人生带来了剧烈跌宕!
没有叩问,就难以走进历史,就无法用历史的语境,厘清其复杂与诡异。
没有悲悯,历史也就没有温度,也就无法找到历史与我们今天的关联。
生逢辛亥,刘庆笃的“命运交响曲”在42岁画上了一个休止符。如果没有那一声枪响,以他的二品之衔,若能外放湖广、两广等地历练历练,这个年纪正是修齐治平的黄金期。然而,历史是没有“如果”的!
让人心生疑问的是“刘庆笃年谱”里显示,他是1914年才回到会宁的。那么,从1911年到1914年的3年,他逗留京城,又在干什么呢?
大勇的文字里,语焉不详。
由于民初的当权者大都在前朝供过职,与进士阶层属于旧雨新知,他们对科举出身的人员比较平和友好,只要稍稍运作,还是能谋到一份差事的。
三年的盘桓与滞留,刘庆笃是难舍难分?还是在寻寻觅觅呢?
让我们将镜头拉回到那些年的北京城:袁世凯、段祺瑞、张勋、徐世昌……一个个政治狂人,把时局整得很乱,把水搅得很浑。从皖系、到直系、奉系,像走马灯似的,不停地换“马甲”,真正是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:狠人上场,猛人翻车,愚人出局,高手登台。时不时地,还有革命党人行刺的夜半枪声。
当然了,作为那个时代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,都面临一场艰难的抉择,是“一臣不事二主”,还是顺时应变,再显身手呢?
古人有以诗述史,以诗代记的传统。或许,我们的问号,在刘庆笃5集的《镜仁堂诗草》中就有抒发和表达,遗憾的是,这本诗集找不见了。抑或是在清末民初与他有过交集的人物史料中有记载。倘有感兴趣者,可循此钩沉。
三、无奈的解药
心病,还要心药治。
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。或曰魏晋风骨,诗酒年华。这些药方,都是现成的。服用与否?刘庆笃在彷徨中犹豫了三年。最终,他远离了庙堂的喧嚣,如同纳兰性德诗中写的:“山一程,水一程,身向榆关那畔行,夜深千帐灯。风一更,雪一更,聒碎乡心梦不成,故园无此声”。我们可以推想,在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,他踩着“七十二道脚不干”的泥泞,回到了祖厉河畔那座弥漫着乡愁的老屋。
他的人生,从此“翻篇”了。
他给自己的书房,起名“懒隐斋”,自题楹联:“引壶觞以自酌,无案牍之劳形”。上联取自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,下联取自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。这,就是解药,他,释怀了。
古往今来,一个人最深的脚印,往往留在最泥泞的路上。
或许今人为刘庆笃叹惋悲悯,只缘刘确属少年得志,起点高,所以期望值就高而已。按常人论,他已经是门楣光耀,可圈可点的人物了。何况,世间没有一马跑出头的人生,每个人都有酸甜苦辣,荣辱沉浮乃寻常事。
归隐后的刘庆笃似乎淡出江湖了。但从后来发生的事,我们可以看出,他想“隐”,也“隐”不了;想懒,还懒不成。他被请“出山”,先是主编纂修《会宁县志续编》,后又担任《甘肃通史稿》总校,还为镇原、隆德等县志以及友人著述作序题诗。
1919年他母亲去世,时任“大总统”的徐世昌送来了挽匾。他在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寄来的剧照上写道:“九畹(梅兰芳,字畹华)云界石根断,寥落西飞雁”。那年头,照相是贵族们玩的事,寄赠照片,胜似今天的名人字画交流,梅氏不避前朝旧臣之嫌,寄来玉照,可见两人交情甚笃。刘比梅年长20余岁,有音乐天赋,时人言其“凡音乐技艺一学即会”。刘善胡琴,两人在京剧艺术方面有很多交流。辛亥年后,刘挂冠归里,梅为其治办行装,剪除发辫。后知刘生活窘困,曾数次邮资接济之。
由此我又萌生一问:1915年12月12日,袁世凯恢复帝制,做了83天的皇帝梦;1917年6月,张勋率5000“辫子兵”,拥戴溥仪复辟,挂了12天的龙旗,等等。身处天高皇帝远的会宁,刘庆笃知道吗?倘若知道,他又会有何反应呢?
耦断了,丝还连否?
1929年(民国十八年),会宁荒旱,地方不宁,刘庆笃旅居兰州。
1936年10月26日,刘病逝于兰州。范振绪撰文追悼,对其一生给予精当评述。省城社会名流如邓宝珊等100多人前去致吊并送挽联挽幛。
呜呼!片云在天,滴水知海。刘庆笃的一生,是那个时代的侧影与折射!
从1936年至今,也不过是八九十年时间,刘庆笃这位会宁近代历史名人的诗词文赋,许多已隐入尘烟,杳无踪迹了。《会宁进士刘庆笃》中着墨较多的还是他的书法作品。身为近臣,他常常书写的是“奉天承运,皇上诏曰”之类的“馆阁体”,这也是他学识渊博,才华过人的一种印证。现存他的书法作品,确如人们所评,有唐楷之功力,欧体之精髓,兼收并蓄颜之深厚,赵之妍美。一言以蔽之,见字如面,圆通工稳。
应该肯定的是,大勇的虔诚与执著,他的专业与特长是中医,但他“勇”于跨界,让人刮目。当然了,这本文集在史料史实的考据、体例章节的布排、文字语法的运用等方面,还需要淘沙沥金,下功夫打磨。还是那句话:瑕不掩瑜。
刘庆笃
□ 周卫宏
北平告急。
一个王朝在你的护持下,
颠簸西来。
车要跑散架了,
马要跑散架了,
你知道,你嶙峋的骨骼千万不能散架。
不需要给你贴什么标签,
改良派也好,保皇派也罢,
那都不能说明你的一切。
你是梅兰芳戏文里的一句唱词,
你拉动的胡琴悠扬里,
还是那段千古佳话。
怎么听,
都像高山流水。
摘自《会宁诗志》